孙首灿|| 论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标准
- 体育资讯
- 2024-12-24 17:11:36
- 14
作者简介:孙首灿,复旦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 《清华法学》2017年第2期。注释已略,引用请以原文为准。
摘要
《行政诉讼法》对于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的规定,从形式上打开了对于抽象行政行为司法监督的缺口。但从目前来看,此项规定的形式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在此之前,法院已对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了"隐性"审查。从以往的案例来看,由于没有完善的审查标准,审查结果以认同行政规范性文件居多,审查往往变成了走过场。相比之下,美国行政规则的司法审查标准比较完善。行政规范性文件类似于美国的非立法性规则,引进美国行政规则审查标准,有助于完善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司法监督,提高《行政诉讼法》修正的实质意义。
一、引言
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行政诉讼法》进行了修改,增加了对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的规定。尽管这次修改不算彻底,在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方式上,没有规定“直接审查”,仅停留在“附带审查”阶段。但“聊胜于无”,这次修改毕竟使得行政相对人可以提出审查要求,法院可以正面对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这也算是我国立法者对于社会长期呼吁的回应。在此次修改之前,由于实际审判工作的需要,法院对于行政规范性文件也进行过“隐性”审查,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于如何审查也有过论述。但总体来说案件数量较少,并且审查标准过于宽松;只要不和法律明显冲突,法院都予尊重,司法审查对于行政规范性文件不能起到很好的监督作用。可以想象,如果继续沿用之前的审查标准,则意味着法院继续“姑息纵容”,即使这次修改导致案件数量增加,但对于改善行政规范性文件司法监督也没有多大意义。
在如何完善行政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标准方面,学界有过广泛的探讨。如有学者认为我国对行政规范的司法审查应以合宪性、合法性和合理性审查为标准,从权限、程序、内容等方面进行审查。权限审查包括“超越职权”和“滥用职权”两方面,程序审查要求遵循最低程度的程序保障标准,即事前的公告通知和公众参与的听证程序,内容审主要是审查是否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相冲突。有学者认为“与上位法不抵触”是行政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的前提标准,在此原则下应根据不同类型采取不同的审查标准:负担性的必须有法律依据,而授益性的则不作要求。此外还存在特例:符合“公共利益”的负担性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必有法律依据,规定“国家标准”之类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效力较高,即使抵触地方法规规章仍应承认其效力。有学者认为行政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采用的是合法性审查标准,但应先经过形式有效性审查后,才能进行合法性审查。合法性主要包括权限合法、内容合法和程序合法。总的来看,上述审查标准在内容上虽然有出入,但在研究视角上具有一致性:即主要探讨了从哪些方面进行司法审查(如合法、合理、内容、程序等方面),而不是将这些方面细化为具体指标,因而可操作性不强。
从世界其他国家来看,一般不通过立法对司法审查标准进行统一规定,而是由法院通过判例逐步形成。在行政权异常强大的中国,法院对于行政规范性文件审查的顾虑重重,消极避让的心态使得少量的审查案例难以形成有意义的司法审查标准。相比之下,美国司法机关对于抽象行政行为审查的历史悠久,积累了丰富的案例资源。本文在对行政规范性文件和美国类似概念比较的基础上,对于美国行政规则的司法审查标准进行重新解读,希望能为完善我国行政规范性文件审查标准提供有益的借鉴。
二、行政规范性文件与美国类似概念比较
(一)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含义
行政规范性文件在我国有多种不同的称谓,有的是法律、法规、规章和司法解释上出现过的概念,如“规范性文件”、“其他规范性文件”、“规范性法律文件”、“行政规定”“规定”、“决定”、“命令”、“指示”等;有的是纯粹的学术概念,如“行政规范”、“行政规则”等。还有“红头文件”等一些非正式的称谓。在其含义上,虽然法律没有提及,但一些地方性规章却进行了界定,如《广东省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第2条规定:“本规定所称规范性文件,是指除政府规章外,各级行政机关依据法定职权制定发布的,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可以反复适用的文件。”《上海市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备案规定》第2条规定:“本规定所称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以下简称规范性文件),是指除政府规章外,行政机关依据法定职权或者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制定的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具有普遍约束力,在一定期限内可以反复适用的文件。”从这些定义来看,行政规范性文件具有非立法性、反复适用性和普遍约束性等特征。即属于具有约束力的除行政立法之外的抽象行政行为。
学界对于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定义与上述行政规章类似,普遍将“约束力”视为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属性,如国内广泛使用的一本教科书在其早期版本中将行政规范性文件定义为:“国家行政机关为执行法律、法规和规章,对社会实施管理,依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发布的规范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行为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政令。”然而,该书后来版本将行政规范性文件分为行政创制性文件、行政解释性文件、行政指导性文件,其中的行政指导性文件不可能具有约束力。与此相对应,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定义也发生了改变,被定义为“行政机关及被授权组织为实施法律和执行政策,在法定权限内制定的除行政法规和规章以外的决定、命令等普遍性行为规则的总称”,不再包含“约束力”特征。
鉴于行政规范性文件种类繁多,“约束力”不应该成为所有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特征。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含义可定义为:行政机关制定的具有普遍效力,针对不特定相对人,可以反复适用的非立法性文件。
(二)美国与行政规范性文件类似的概念
由于国情的不同,美国不可能具有和行政规范性文件内涵完全相同的概念。但基本符合非立法性,具有普遍效力,可以反复适用等特征的抽象行政行为还是存在的。美国《行政程序法》(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Act)对于“规则”(rule)进行了界定:“机关为执行、解释、说明法律或政策……而发布的,普遍适用或专项适用并将生效的陈述性文件的全部或一部。”其中的“普遍适用”和“专项适用”体现了适用范围标准,“将生效”体现了时间标准。“从这个规定中可以看出,法规(本文译为“规则”)不仅指行政机关作出的普遍适用的决定,而且还包括它们作出的适用于特定人或特定情况的决定在内。但是由于法规(规则)只适用于将来发生效力的决定,所以现在和过去发生效力的具体行政决定不是法规(规则),这样就把法规(规则)和绝大部分行政裁决分开了。” “‘专项适用性’规则的提法似乎与规则的概念恰好相反,这是由于历史反常的原因。之所以如此规定的目的在于维护一种传统的理解,即费率诉讼应被视为规则制定过程而非审断。”由此可见,虽然“规则”也有适用于个别的特殊情况,但绝大多数是普遍适用的。因而绝大部分规则属于抽象行政行为。
美国《行政程序法》中出现的规则种类主要有实体性规则(substantive rule)、解释性规则(interpretive rule)、政策说明(statements of policy),并规定实体性规则一般要按照该法规定的制规(rulemaking)程序制定,而解释性规则和政策说明一般免予制规程序。但《行政程序法》仅对“规则”(rule)和“制规”(rulemaking)进行了界定,并没有定义各种类型的规则,也没有说明它们是否有约束力。该法颁布一年之后制定的《关于行政程序法的司法部长手册》(Attorney General’s Manual on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被认为是对《行政程序法》原意进行解释的最为重要的文件,对于各类型行政规则的含义进行了阐述,认为实体性规则是行政机关根据法律授权发布的……执行法律的规则;解释性规则是告知公众行政机关对其所执行的法律和规则的理解的规则;政策说明是告知公众行政机关将如何行使其自由裁量权的规则。司法部委员会(Attorney General’s Committee)关于行政程序的《最终报告》(final report),也对解释性规则和实体性规则进行了描述,将解释性规则描述为:主要具备“建议”性质,仅表明机关对于法律语言目前的理解,并不能产生约束力,如果在法律应用上有不同意见,应交由法院决定。将实体性规则描述为:许多法律条款只有在行政规则制定之后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对不遵守者施加惩罚或不予好处,此种行政立法具有强迫遵守的制裁力量。因此,此类实体性规则具有法律的许多属性,被称为次级立法(subordinate legislation)。
美国学界一般将具有法律效力的实体性规则称为“立法性规则”(legislative rule),将解释性规则和政策说明称为“非立法性规则”(non-legislative rule),但《行政程序法》并没有使用上述概念。一般认为,立法性规则依法律授权发布,并按照《行政程序法》的制规程序制定。由于立法性规则影响“个体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属于实体性规则。立法性规则本质上属于行政立法,具有完全的法律效力,对于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都具有拘束力。非立法性规则是行政机关没有依制规程序发布的声明,既不是法律授权发布,也不改变个体的权利。因此,非立法性规则对于公众并不具有约束力。联邦法院将非立法性规范分为解释性规则和政策说明。解释性规则是对当前法律规定进行解释,但不增加新的规定。政策说明是行政机关在扮演各种行政角色时,告知公众其行使裁量权的愿望和意图。
将美国的《行政程序法》和我国的《立法法》进行比较,两者都规定了行政立法的种类和制定程序。不同之处在于,《行政程序法》对于免予立法(制规)程序的解释性规则和政策说明有所提及;而《立法法》在行政立法方面只提到了行政法规和规章,根本没有提及行政规范性文件,这也从反面证实了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属于行政立法的范畴。从适用行政立法程序的角度来讲,美国行政规则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立法性规则,主要是指《行政程序法》中的实体性规则,要按照制规(立法)程序制定,大致相当于我国《立法法》中的行政法规和规章;二是非立法性规则,主要是指《行政程序法》中的解释性规则和政策说明,不用遵守制规程序,大致相当于我国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三、行政规范性文件法律效力的探讨
根据我国的行政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模式,行政相对人在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可以附带对作为该行为依据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含国务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提出审查要求。按照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作为行政行为依据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其本身要合法有效,这就涉及了对行政规范性文件法律效力的判断。
对于抽象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中出现了“依据”、“参照”和“审查”三种判断方式。《行政诉讼法》(2014年)第63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参照规章。”第64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中,经审查认为本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的,不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并向制定机关提出处理建议。”
一般认为,“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是指法院一定要适用,没有任何选择或灵活处理的余地,即法院要无条件的承认法律和法规的法律效力。“参照规章”赋予了法院审查权和选择权,规章对法院是缺乏强制拘束力的,即法院对于规章的法律效力可以自行判断。
对于(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审查而言,主要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行政立法性文件的有权解释机关进行解释所形成的规范性文件(下文称“正式行政解释性文件”),视其与所解释的行政立法性文件具有同等效力。《座谈会纪要》的第一部分“关于行政案件的审判依据”中规定:“……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公布的行政法规解释,人民法院作为审理行政案件的法律依据;规章制定机关作出的与规章具有同等效力的规章解释,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时参照适用。”另一种是“正式行政解释性文件”之外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下文称“一般行政规范性文件”),法院有权对其效力进行判断。由于存在上述区分,下文将对这两类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法律效力分别予以探讨。
(一)一般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法律效力
对于行政规章和一般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法律效力,法院可以进行审查判断。但在对于这两种类型文件法律效力的区分,没有官方文件进行区分,也鲜有学者进行论述。美国的立法性规则相当于我国的行政规章,非立法性规则相当于行政规范性文件,因此,可以借鉴美国对于立法性规则和非立法性规则法律效力的审查经验明确一般行政规范性文件法律效力的审查标准。
1.对于非立法性规则的Skidmore尊重原则
法院对于非立法性规则的审查强度,体现了法院对其法律效力的认可度,也就是尊重程度。美国主要是通过1944年的Skidmore v. Swift & Co.案进行确立的。
Skidmore案并非一起行政案件,而是一桩劳资纠纷案。案件源于Swift & Co.包装厂与其厂里7名工人达成的一项口头协议,内容是这7名工人每周在厂里值三四天晚班,负责响应火警。这7名工人认为响应火警的等待时间也属于工作时间,因为这份协议违反了《公平劳动标准法》(Fair Labor Standards Act)。为了得到厂方的赔偿,工人向法院提出了诉讼。这起案件的关键在于对“工作”一词的理解:即为响应火警而等待的时间是否构成工作时间。在此案发生之前,劳工部的工资与工时局(Wage and Hour Division)曾发布一份解释性公告(Interpretative Bulletin No.13),对于等待时间是否构成工作时间进行了说明。但一、二审法院并没有考虑公告的意见,径行认为等待时间不构成工作时间。最高法院通过采用公告意见得出结论,认为等待的时间并非必然不构成工作的时间,但是本案中的等待的时间不构成工作的时间。
最高法院在判决书中对于解释性规则的效力进行了论证,认为本案中所涉及的解释性公告,尽管不能因为其权力对法院有约束力,但的确可构成法院和诉讼当事人可以正当地获得指导的一套经验和有见地的判断,并提出对于解释性规则效力的判断标准:在某一特定案件中的此类判断的分量,将取决于其考虑所表现出彻底性、其推理的有效性、其与先前和后来的声明的一致性,及所有可获得说服力的这些因素。美国学者称之为Skidmore尊重标准(Skidmore deference)。
从对解释性规则法律效力的判断标准来看,Skidmore尊重只是一种轻度的司法尊重。解释性规则对于法院来说“具有说服力,缺少约束力”,法院既不能无视解释性规则的存在,也不能受其束缚,应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其法律效力。因此,对于解释性规则的法律效力,法院具有巨大的裁量空间。
2.对于立法性规则的Chevron尊重原则
美国对于立法性规则的尊重程度高于非立法性规则,因此在审查标准上相对宽松。这主要是因为立法性规则的制定要经过“通告和评议”(notice and comment)程序或者听证(hearing)程序,这意味着立法性规则经过了事先的民主监督,因此事后进行严格的司法审查就变得没有必要。美国立法性规则的审查标准是通过Chevron案确立的。
Chevron案源于环保部为执行《1977年清洁空气法修正案》(The Clean Air Act Amendments of 1977)而颁布的一项立法性规则。1977年,为了提高环境质量,议会通过了《清洁空气法》的修正案。该修正案要求没有达到环保部制定的国家空气质量标准的州,建立起废气排放许可制度,目的在于调控“新的或改进的主要固定污染源”(new or modified major stationary sources),并规定一般在严格达标后才可颁发许可证。1981年,环保部颁布了执行废气排放许可的立法性规则,引入了“气泡”(bubble)概念。即各州可对“固定污染源”采用以整个工厂为审核单位,如果整个工厂的排放总量不增加,对于其中的单个没有达到许可要求的污染设施可以进行任意的添加或改动。也就是说,允许州将位于同一工厂区内所有的污染设施视为一个整体(如同一个“气泡”)。这对于要求单个设备都要达标来说,无疑是降低了许可标准。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作为一个保护环境的公益组织,认为该规则纵容了环境污染,于是向上诉法院提起司法审查,上诉法院以“气泡”概念违法为由将该规则撤销。上诉法院认为,尽管《清洁空气法修正案》没有清晰定义“固定污染源”,这个问题从立法史也不能直接找出答案,但鉴于许可设置的目的在于改善而不是仅仅保持空气质量,以工厂为单位的定义是不恰当的,因为这种方法是用来维持空气质量现状。作为利害关系方的Chevron公司随后对案件提起上诉,最高法院最终支持了环保部对于“固定污染源”解释的立法性规则。
在此案中,最高法院建立了两个步骤审查标准。第一步,要看“国会有没有直接表达对问题的看法”。如果国会的意图是清楚的,那么“事情就解决了,无论对于法院,还是行政机关,都必须执行国会明确表示的意图”。第二步,如果法律对此“沉默或模糊”,要看“行政机关的答案是否基于对法律可行的解释”。换句话说,“如果法律的含义不清楚,法院必须接受行政机关合理的解释”,这种高度尊重使得行政机关的解释具有实际上的约束力。美国学界将该标准称为“Chevron尊重”(Chevron deference)。
关于上述判断标准的适用范围,该案判决中并没有明确,后来的United States v. Mead Corp.案将其适用范围仅限于立法性规则,也就是对于非立法性规则不能适用Chevron高度尊重标准。这就意味着,如果行政机关“合理的解释”以立法性规则的形式作出,即使法院可能对此有不同的理解也要接受。这种分析框架基于如下观念:当行政解释涉及运用政策制定裁量权时,法院应接受具有一定民意基础的合理行政决定,这与宪政基础较为一致。
参照上面的案例,对于类似于美国立法性规则的行政规章,法院审理时所谓的“参照”可理解为采取“合理性”标准,即只要行政决定有可能正确,从而达到一个“良好判断(sound judgment)”,就应承认其法律效力。对于类似于美国非立法性规则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法院的“审查”应理解为采取“说服力”标准,即只有“行政决定正确的可能性大于错误的可能性”,才能承认其法律效力。行政规章属于行政立法,其制定要遵循《规章制定程序条例》,制定过程中有类似于美国的“通告—评论”等公众参与环节,因而经过了民意审查;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程序没有立法进行统一规定,其制定相对随意,没有公众参与的必然环节。因此,法院理应对行政规范性文件采取较为严格的审查标准,在不具备“说服力”的情况下,不能轻易承认其法律效力。
(二)正式行政解释性文件的法律效力
在明确了“依据”和“参照”的基础上,正式行政解释性文件的法律效力似乎可以确定。但对于正式行政解释性文件为何具有与其所解释的行政立法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问题,《座谈会纪要》指出是“根据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关于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解释的规定”。从实证法层面来讲,这种理由是成立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具备足够的法理基础。
从制定程序来说,现行法并没有将正式行政解释性文件和一般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区分,实际区分标准仅为制定主体和其制定意愿,也就是说具有正式解释权的主体根据其自身意愿来决定是否制定正式行政解释性文件。一般来说,行政立法性文件的制定主体行政级别较高,如果因此认为其解释水平也高,那么无疑是“等级特权”思想在作祟。如果认为行政立法的制定者会更了解立法的真实意图,因此所作的解释更符合立法原意,这种理由似乎还算成立。但会不会出现行政机关为了避免繁琐的立法程序,故意制定含义模糊的立法条款,然后再通过发布正式解释性文件,从而替代行政立法呢?美国也存在行政机关对其立法性规则进行解释的情形,对于这种解释性规则的法律效力问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
1.对于行政解释高度尊重的Seminole原则
美国最高法院通过Bowles v. Seminole Rock & Sand Co.案,表达了和我国上述司法解释同样的观点。该案案情大致如下:物价局(Office of Price Administration)根据《1942年物价紧急管制法》(Emergency Price Control Act of 1942),通过制规程序制定了名为《最高价格条例》(Maximum Price Regulation)的立法性规则。随后,物价局根据其中的第188条对于Seminole砂石公司进行了制裁。该案的关键在于如何对《最高价格条例》第188条进行解释。最高法院以“对于行政机关的解释,必须给予‘约束力’,除非明显错误或与所解释的立法性规则不一致”为由,认可了物价局的解释,判决物价局胜诉。由此确立了对于行政机关对其立法性规则所作的解释,给予高度尊重的Seminole原则。
对于该案所确立的审查标准,美国学界争议很大。有学者认为最高法院采取了“不符合逻辑并且反民主的立场”(illogical and highly anti-democratic position)。这种审查标准使得推翻行政机关对其立法性规则所作的解释变得几乎不可能,尽管通常情况下,这种解释以非常不正式的方式作出。这种“自损身价”(abject mode)的司法尊重模式,给予行政机关实际上约束人民行为的权力;只要行政机关先前发布过立法性规则,随后对该规则进行解释即可,法院连解释的“合理性”都不作要求。正因为如此,这种尊重模式实际上鼓励了行政机关发布模糊的立法性规则,需要时再发布解释性规则进行明确。当立法性规则模糊,存在多种解释的可能时,这种高度尊重原则意味着:在没有事先的公众参与和事后司法审查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可以随意创制义务。
Seminole案的判决发生在《行政程序法》颁布之前。从《行政程序法》第706条的规定,即“负责审查的法院……确定机关行为术语的含义或适用性”来看,Seminole尊重也是违法的。因为这项规定的意图很清晰:法院才是立法性规则的最终解释者。当对于立法性规则有多种解释时,行政机关倾向于作出对自身有利,对行政相对人不利的解释。因此,行政相对人应该具有在法院挑战行政机关解释的权利。当然,法院对双方的争议应居中裁判,在Skidmore原则下给予行政机关解释应有的尊重。
2. Piccotto案对于Seminole原则的限制
对于Seminole原则,美国法院后来通过Piccotto案进行了限制。Piccotto案的大致情况为:美国公园管理处(United States Park Service)经过通告评论程序,发布了首都公园管理规则,对于示威和一些特殊事件进行限制。其中规定了一些特定情形下的行政许可,并规定可以包括一些“其它的合理情境”(additional reasonable conditions)。国家首都公园地区主任(The Regional Director of National Capital Parks)根据此条款规定了一些“其它的合理情境”,但这些却没有经过通告评论程序制定。Piccotto 就是因为违反了这些“其它合理情境”中的规定而被捕的。审理案件的法院认为,这个案件涉及行政机关免予《行政程序法》规定的制规程序的问题,并认为《行政程序法》为了平衡行政效率和开放、透明政府的目标,只在特定情形下才允许行政机关绕过既定的制规程序。行政机关不能对于“其它合理情境”这种开放条款进行解释,用以限定特定情况。
很多其他法院也认为行政机关不能采用公园管理处的做法,原因在于:《行政程序法》关于规则的制定程序,用途在于使行政机关通过该精心设计的程序,把法律模糊的规定转变为清晰合理的行政规则。如果法院允许行政机关制定模糊开放的立法性规则,并承认对该规则解释的非立法性规则具有法律效力,那么就意味着同意行政机关绕过《行政程序法》,通过制定模糊的立法性规则,来执行模糊的法律。因此,Piccotto案实际上确立了行政机关不能通过解释性规则,将含义模糊开放的立法性规则进行具体化的原则。这样就大大缩小了Seminole尊重的适用范围。
由此可见,对于正式行政解释性文件的审查,在美国存在Seminole尊重和Skidmore尊重之争。尽管法院没有废除Seminole尊重原则,但通过Picciotto案大大限制了其适用范围。从法理上讲,Skidmore尊重似乎更能站得住脚。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角度出发,我国对于正式行政解释性文件,应该采取Skidmore尊重原则,即采取“说服力”标准,只有“行政解释正确的可能性大于错误的可能性”时,才能承认其法律效力。
四、行政规范性文件“解释”与“创制”的区分
我国学界一般将行政规范性文件分为“行政创制性文件”、“行政解释性文件”和“行政指导性文件”,认为行政创制性文件是指行政机关未启动立法程序而为不特定相对人创设权利义务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行政解释性文件是对法律、法规和规章进行解释而形成的规范性文件,行政指导性文件是行政机关对不特定相对人事先实施书面行政指导时所形成的一种行政规范性文件。与美国相比,行政解释性文件与解释性规则类似,行政指导性文件与政策说明类似,但行政创制性文件和实体性规则不能等同。因为实体性规则属于行政立法,而行政创制性文件则属于行政规范性文件,即除行政立法之外的抽象行政行为。
在美国,除了实体性规则(属于立法性规则)可以设定权利义务外,解释性规则和政策说明(两者都属于非立法性规则)均不可设定权利义务,也就是说美国的非立法性规则不可能包含行政创制性文件。在中国,作为非行政立法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之所以能够创设权利义务,主要是由于我国法治程度低的缘故。因为从根本上说,公众的权利义务应当由法律、法规和规章来创制。行政规范性文件创制公众权利义务应当是一个例外。就目前来讲,我国创制公民义务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大多声称“依据”法律文件(即法律、法规、规章),以独立的名义来创设公民义务的情况并不多见。但何谓“依据”,从我国官方文件和法院的判例中很难找到判断标准。按照依法行政的要求,规定公民义务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其效力只能归于法律文件,也就是只能是对于法律文件的解释。但“解释”到何种程度,不至于变成“创制”,这就涉及了“创制”和“解释”区别问题。美国对于非立法性规则的审查,主要是围绕着“解释”和“创制”的区别展开。
美国法院在审理非立法性规则是否有效的案件时,倾向于首先询问该规则是否具有约束力。在没有经过通告评论程序的情况下,行政机关能够参与政策制定(通过发布“政策说明”),只是不能对自身和公众产生约束力。如果非立法性规则产生约束力,只能归于其对现行法的解释,而不是独立的政策制定。这种文件必须是真正意义上的“解释性规则”。如果行政机关在没有经过通告评论程序就可以制定具有约束力的行政规则,那么它就没有采用繁琐制规程序的动力。然而,“解释”和“创制”的界限越发细微,在案例中经常出现两者模糊不清的情况。原因在于,解释性规则没必要仅仅重复法律和立法性规则的内容,否则就几乎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相反,行政机关可以依靠解释性规则来“解决……歧义”,或者将“模糊的权利义务界定清晰”。现代解释理论认为,解决歧义问题几乎总是涉及一定程度的政策制定裁量。因此,需要有一套标准来区分“解释”和“创制”。这种区分标准在美国是通过案例确立的,并且随着时代的不同,案例采用的标准会有所变化。
(一)“美国采矿协会案”确立的区分标准
美国法院对于形式上的非立法性规则(没有经过制规程序发布)的审查,是围绕着规则实质属性展开的,即规则在实质上属于立法性规则(创制了新的权利义务),还是属于非立法性规则(对原有立法的解释性)?通常是行政相对人声称规则的立法属性,而行政机构则坚持规则的非立法性。这种争议分为两种:一种是行政相对人想从程序的角度论证行政规则的无效性,声称因为行政机关没有经过通告评论程序,规则所以是无效的。行政机关则回应称规则是解释性规则或政策说明,因此不需要经过通告评论程序。第二种争论涉及行政机关的行为违反了行政规则,行政相对人认为该行为因违反规则而无效。行政机关则回应称该规范是非立法性规则,对于行政机关没有约束力。
“美国采矿协会案”(Am. Mining Cong.v. Mine Safety & Health Admin.)争论的焦点就在于矿山安全和健康管理局(Mine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简称“MSHA”)发布的非立法性规则,实质上是否属于立法性规则。《矿业安全与健康法》(The Federal Mine Safety and Health Act)要求矿主“按照劳工部长(Secretary of Labor)的合理要求,进行……的汇报”,并广泛授权劳工部长发布“为执行法律条款所必需的”行政规则。MSHA(代表劳工部长)发布立法性规则,要求矿主汇报“在矿里发生的职业病”,其中包括要求矿主尽早汇报每一例确诊的尘肺病(pneumoconiosis)。MSHA对于立法性规则中的模糊之处,时常以“项目政策信”(Program Policy Letters)的形式进行解释(没有经过制规程序)。多年后,MSHA发现矿主在何时汇报确诊的尘肺病时采用不同的标准。MSHA针对这个问题,发布了关于尘肺病确诊标准的项目政策信。该信件采纳了国际认可的X光胸透12步系统,评级在1/10或以上者被认为是尘肺病。这就意味着矿主必须依该信件采纳的确诊标准及时上报病情。
美国采矿协会对于信件扩大X光数据要求的合法性提出质疑,认为该信件属于立法性规则,需要经过“通告—评议”程序违法。因此,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认为MSHA信件没有经过通告评论程序,因而属于程序违法。法院面临的问题是:MSHA关于肺病诊断的信件是否属于《行政程序法》中的解释性规则?MSHA的信件要求矿山所有者对于在开矿中特定的肺病遵守严格的报告制度,对于所要求的X光数据读取设立了具体的程序。
对于法院而言,如果仅从字面分析规则的属性是困难的。解释性规则“解释”已有的立法性文件,不“创制”新的内容,但立法性规则也经常“解释”词句的意思。因此,从词源学方法上无法明确区分行政机关是在制定新法,还是在澄清已有的法律。面对这一难题,法院转向了行政机关的意图。
如果一个行政机关声称其规则具有法律效果,法院可以简单地认同其声明。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行政机关没有动力去谎称其意图。只有得到国会授权,并且遵循通告评论程序,行政机关发布这样的规则才合法。如果行政机关声称其发布的是解释性规则,这时候法院就不能简单地采纳行政机关的描述。在这种情况下,行政机关有动力将立法性规则错误的描述为解释性规则,以避开《行政程序法》规定的制规程序。因此,法院必须进行检验——如果规则合法,是否具有“法律效果”——来判断一个假定的解释性规则是否实际上是程序缺失的立法性规则。这就需要法院找到“规则如果合法,就具有法律效果”的情景。
法院进一步论述了形式上是非立法性规则,实质上属于立法性规则的情境,形成了“法律效果”测试(“legal effect” test)方法(标准)。对于一个行政机关声称的非立法性规则,通过以下检验标准,便可以确定其实质属性:
(1)在缺少该规则的条件下,行政机关的执行、授益、或履行职责是否会缺少足够的法律基础?(2)是否在《联邦行政法规汇编》(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简称“CFR”)上发布?(3)行政机关是否清晰地援引其一般立法权限?(4)是否该规则有效地修正了之前的立法性规则?
如果对于这些问题回答“是”,则行政机关意图具备法律效果,该规则实为立法性规则,应当采取《行政程序法》中规定的制规程序制定。按照上述标准进行检验,法院得出“项目政策信”是合法解释性规则的结论。理由是:第一,信件中所要求的报告,并不是填补立法的不足来作为执行的依据。也就是说,在没有该信件时,矿主也要进行报告。第二,行政机关意图并非是作为立法性规则,因为既没有在《联邦行政法规汇编》(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上公布,也没有援引一般立法权限。最后,该规则并没有修改矿山安全和健康管理局的之前的立法性规则,它仅仅是对之前规则的进一步补充和明确。
(二)“法律效果”标准的演变
“法律效果”标准并非一成不变,美国法院后来多次对该标准进行修正,有的被学界广泛赞同,但有的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1.删除“在CFR上发布”,增加“开放性”判断标准
如果一个行政规则“在CFR上发布”,以此就认为属于立法性规则,那么这种判断标准就太过僵硬了。因为存在明显的不合理性,法院后来就通过Health Insurance Ass’n of America, Inc.v. Shalala案删除了该标准。该案由保健财政管理局(Health Care Financing Administration)代表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Secretary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发布的5部行政规则引起,美国健康保险协会(Health Insurance Ass’n of America)质疑这5部规则的有效性。法院在本案中论述了行政规则的审查标准问题。
法官认为在CFR上刊登不再是“一条关于行政机关意图的证据(a snippet of evidence of agency intent)”。法院列出了两条删除理由:第一,一个解释性规则也具备发布条件,只要该规则具备“法律意义”(legal effect),尽管不具有法律效力(the force of law)。一个规则可以具备多种“法律意义”。所有解释性规则至少具备一个重要的“法律意义”:它们为潜在受影响者提供行政机关对于法律或立法性规则理解的信息。因此,解释性规则也适合在CFR上发布。第二,很多行政机关有在CFR上发布最为重要的解释性规则的习惯。这种行为对于社会是有益处的,因为这样可以使受影响的公众能够知晓最为重要的规则,不管是立法性的还是解释性的。此外,法院还担忧,如果认为在CFR上发布就断定是立法性规则的话,那么会使得行政机关不愿再公开发布其解释性规则。
在“美国采矿协会案”,法院提到了另外一个虽然不适用于本案,但确有广泛适用性的判断标准,即“如果一个规则对于模糊开放的立法性规则进行具体规定,那么这个规则属于立法性规则”。对于该判断标准的合理性,法院主要通过引用Piccotto案进行论证,前面第三、(二)2.部分已介绍了案情,这里不再赘述。
2.增加“修改解释性规则的也是立法性规则”的判断标准
从解释性规则的属性来看,因为“解释”是要阐明所要解释规则的原意,而不是“创制”新的规则。因此,解释性规则只能对立法性规则进行解释,而不能改变立法性规则;能够修改立法性规则的只能是另一个立法性规则。一般认为,解释性规则能够改变之前的解释性规则是不言而喻。然而,在“阿拉斯加猎户”(Alaska Professional Hunters Assn v.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案中,法院却表达了行政机关不能通过解释性规则改变之前发布的解释性规则的观点。该案的基本情况为:联邦航空管理局(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在早期的立法性规则中,对飞机“商业运营者”(commercial operator)进行了界定:指任何人,无论是通过飞机运输人员或者是货物,只要是以收费或雇佣为目的。1963年,联邦航空管理局进行了解释,认为如果运输在飞行员的向导工作中“仅仅是偶尔发生”,则不在其内。因此,根据此项解释,将阿拉斯加州的捕猎和捕鱼向导将其客户带往目的地的行为,排除在了需要获得商业飞行执照的范围。这些向导不需要遵守有关商业飞行员的规定,尽管他们以“收费和雇佣”为目的运输人员。1998年,联邦航空管理局在联邦登记(Federal Register)上发布了“告知飞行员”(Notice to Operators)的通知,宣布废除1963年的解释。在其发表的新解释里,将“商业运营者”的概念,包括了所有通过飞机运输客户并“收费或提供雇佣服务”的向导,认为这样做有助于提高飞行安全。阿拉斯加专业猎户协会则认为,该“通知”实际上是立法性规则。因此,在没有经过通告评论程序下是违法的。联邦航空管理局则认为是解释性规则。法院认为通知属于程序非法的立法性规则,因为行政机关不能通过解释性规则改变之前关于立法性规则的解释。
对于“只有立法性规则才能修改之前解释性规则”的观点,美国有些学者持反对态度,如认为这种观点无论是从制定法、案例法,还是从逻辑上都站不住脚。但如果从“信赖保护”的角度来看,这种观点却具有合理性。如果基于对解释性规则的信赖,人们已经形成了该规则所认可“利益”,那么行政机关就不能随意撤销该规则。如果之后制定规则要对该利益进行减损,则意味着减少公民的权利或增加其义务,因而此时的解释属于“创制”义务,而不是单纯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理应提供公众参与规则制定的机会;采用通告评论的制规程序来制定立法性规则进行改变,也是“正当程序”原则的要求。再者,改变公民权利义务的只能是实体性规则,通过解释性规则进行改变是不恰当的。因此,通过立法性规则来改变之前解释性规则,能够更好地保护公民的权利。
综上所述,在“美国采矿协会”案确立的“法律效果”标准基础上,删除“在CFR上发布”,增加“开放性”判断标准和“立法性规则修改解释性规则”的标准,“法律效果”标准演变为:
(1)在缺少该规则的条件下,行政机关的执行、授益、或履行职责是否会缺少足够的法律基础?
(2)行政机关所解释的立法性规则是否太模糊或开放,以至于不能支撑解释性规则?
(3)行政机关是否清晰地援引其一般立法权限?
(4)是否有效地修正了之前的行政规则(不论之前的规则是立法性规则,还是解释性规则)?
如果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该规则应是立法性规则,其特征是“创制”新的权利义务;如果上述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那么该规则是非立法性规则,其特征是“解释”已有的立法(解释性规则)或表达其倾向性意见(政策说明)。因此,通过“法律效果”标准,就将“创制”和“解释”的界限进行了区分。
(三)“法律效果”标准在我国案例中的运用
从“法律效果”标准的内容来看,是一种较为严格的审查标准。美国法院对于立法性规则的尊重程度高于非立法性规则,“法律效果”标准在适用范围上只限于非立法性规则,而不是适用于立法性规则。该标准应用的前提是立法性规则和非立法性规则在创制公民义务上的区分,如果我国也严格遵守美国类似的逻辑,即只有行政立法才可以“创制”公民的义务,行政规范性文件只能“解释”已有的立法,其约束力只能归于对立法性文件的解释。那么,在区分“解释”和“创制”方面,“法律效果”标准也可以应用于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审查。
1.“法律效果”标准在“汽车尾号限行案”中的应用
2008年9月,北京市政府发布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下文简称《通告》),要求自2008年10月至2009年4月期间,本市机动车须按车牌尾号每周停驶一天,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负责具体实施。随后,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于2008年12月发布了《关于机动车按车牌尾号每周停驶一天轮换停驶日及2009年春节期间有关规定的公告》(下文简称《公告》),对于限行号码、路段和时段进行了具体规定。2009年1月,张兴驾驶车在限行路段行驶时,被交警告知其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39条,以及《通告》和《公告》的规定,依据《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91条第4项的规定,对其罚款100元。张兴不服交通管理部门依据《通告》对其作出的处罚决定,以《通告》中尾号限行和《道路交通安全法》中的限制通行不一致,《通告》不是法律、法规、规章,处罚决定缺乏法律依据为由,提起了行政诉讼。法院经审理认为,《通告》是北京市人民政府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办法》的有关规定制定的,目的在于减少机动车尾气排放对空气质量的影响,保持交通基本顺畅。交警依据《北京市实施道交法办法》第91条第4项的规定,对张兴处以100元罚款,并无不当。
交警处罚的依据是《北京市实施道交法办法》和《通告》,前者为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行政处罚;后者为行政规范性文件,按照《行政处罚法》不得设定行政处罚。由于《北京市实施道交法办法》没有对于限行进行具体规定,张兴直接违背的是《通告》,而不是《北京市实施道交法办法》。因此,该案审理的关键在于对“依据”的理解,也就是说《通告》的限行规定是对《北京市实施道交法办法》的“解释”,还是自行“创制”。如果是“解释”,那么《通告》的效力可以归于《北京市实施道交法办法》,就可以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否则,就是在“创制”行政处罚,违背了《行政处罚法》。遗憾的是,法院在本案中并没有对“创制”和“解释”的区分进行论述,就直接以“依据”合法为由,承认了《通告》的效力。
在本案中,判断《通告》是“解释”还是“创制”,需要对于《通告》的性质进行判断。如果《通告》名为行政规范性文件,实质上却是具有“法律效果”的行政立法,那么《通告》则是“创制”而非“解释”上述立法性文件。按照“法律效果”标准,进行逐条检验,其结果如下:
(1)如果缺少《通告》,则交警对于张兴将无从罚款,即“对于行政机关的执行、授益、或履行职责将缺少足够的法律基础”。

下一篇:犯罪嫌疑人游街示众是否违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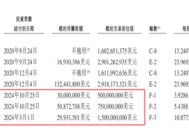









有话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