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后的科技对话导演方励:人类没有未来
- 欧洲杯直播
- 2024-12-26 20:18:53
- 10
文 | 硅谷101
当方励决定将一艘沉睡82年的二战沉船“里斯本丸”从海底“打捞”上银幕时,他面临着一个意想不到的挑战:最先进的特效反而阻碍了观众去聆听幸存的老兵和家属的声音。经过多轮试错后,他决定将耗时一年、耗资2000万搭建的精细三维建模简化为直白的版画风格,让观众的注意力重回《里斯本丸沉没》的历史录音与口述实录。
作为中国知名导演兼制片人,方励制作拍摄了《后会无期》《乘风破浪》《观音山》《苹果》等多部电影,同时他也是地球物理学、海洋技术与无人系统领域的专家。上世纪80年代,方励因工作机缘踏入硅谷,那个年代的互联网还未崛起,硅谷却已是电脑与高精仪器制造的热土。此后数十年,他目睹了硅谷的剧烈变迁:从硬件工程到软件革新,从互联网泡沫到人工智能热潮。
在方励眼中,AI是高效而强大的工具,但无法取代和创造人类的真实感情和表达。在见证了一轮又一轮科技的变革后,他对人类技术发展的终局并不乐观,甚至觉得“人类没有未来”。但这不妨碍他一直做自己喜欢的事,年满71岁的他正在策划最具挑战性的项目:寻找消失近十年的马航MH370。
“这就像登珠峰,”方励说,“也许永远到达不了顶峰,但尝试本身就很有意义。”
以下是部分访谈精选
泓君:最早您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机缘下来到硅谷的?
方励:1985年的时候,我为一个美国的上市企业工作,过来访问。那时候第一次来美国,跑了20多个州。最后跑了一圈,从美国南部、中部、东部一直到西海岸,最后留在硅谷待了两个礼拜。发现这个地方天气也好,人文环境也不错。那个时候Fry’s Electronics只有很小一个店面,但是自己可以攒电脑了,这在1985年已经很惊人了。那个时候91年年底把工作辞了,自己创业,那就往返中国美国,跑了20多年。过去这十来年基本上待在北京比较多了,因为我又做电影又做科技。我从14年前开始就做无人系统,无人系统在天上飞的,我跟我的比利时合作伙伴一起:单桨的无人直升机,做勘探、做遥测、遥感,然后能干水面的无人艇、水面机器人,这些都有涉及。
泓君:这些机器都是您自己造的?
方励:对啊,我自己设计啊,因为是我的兴趣爱好。现这边我们做水下机器人嘛,原来这个公司在San Leandro,以前我是他们代理商,后来把它收购了,然后就开始自己设计制造。现在我把生产搬到国内去了。美国这边就留销售和售后服务。所以硅谷这个地方太熟悉了。我在90年代跟UC Berkeley做,还有Lawrence Berkeley实验室都合作,那做油气勘探的井中电磁成像,做电磁系统。那跟Stanford合作,那个时候跟地球物理系做过他们岩石物理实验室的五年顾问。那个做digital rock都是做油气勘探的,深部地壳探测等。
泓君:您从80年代到90年代在硅谷的时候,因为当时互联网还没有起来。当时硅谷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方励:硅谷当时也很热闹,那当年主要是电脑,原来的惠普、苹果都在这。苹果以前的名字还是Macintosh(麦金塔),然后最后又改回来了。还有Sun Workstation (太阳工作站,后被甲骨文收购),Sun Electronics (同属于Sun公司,已经被收购),那是都在这,但做各种仪器的比较多,各种科技仪器制造工业、研究和制造。那个时候软件还没有那么时尚,也没有互联网。有了互联网了以后的变化就非常大,从硅谷最火爆的时候,一直到最后互联网泡沫破裂。
泓君:您看到的整个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的这段历史,再对比到过去两三年,其实是一个AI的热潮年,它可能又是硅谷的一个小的,大家都非常疯狂的一个热门行业。
方励:AI就是个很好的工具,因为计算速度快了,存储量大了,功耗低了。既然叫人工智能,它是人工的,它就不是原创的东西。它一定是把别人所有做过的东西都放在你的文件夹里面、数据库里面,非常快速的交叉调用、交叉组合。所以呢,对于我们大家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
泓君:您觉得这一轮的生成式AI跟你之前提到的这一类的AI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
方励:速度快了,你交叉的速度快了。其实就很简单,就是相当于你有1亿个眼睛同时在看,就出来各式各样的东西。他就把人类做过的所有的东西都非常快速的存储起来。但是最要命的问题,未来呢,人不创造了,都AI去了,人都没有智能了。你现在人工智能依赖的全部都是100%的前人做过的工作,你把它借鉴过来了。但是如果久而久之,我们只是用AI彼此去产生各种怪胎,假如说我们人都过度的依赖AI,人的创造力没了,这特别恐怖。小孩子的教育怎么办?大家都AI,还有原始的创造力吗?
泓君:所以这个看是工具用人,还是人用工具吗?
方励:太对了。前两天我在参加金鸡奖,我看他们在台上就讲的AI就特别热闹。有一哥们直接讲的是以后用AI,演员都失业了。我说你说啥呀?人是千差万别的,各种各样的情绪,他的魅力就来自于他独特的个性。以后我们都用AI生成假人去表演,那你不是糊弄观众吗?那就是你全部都是模仿的、仿造的和畸形的,没有个人生命力。当然你可以出来各式各样的幻觉和奇葩的幻象,但是人的艺术感和生命力去哪里了呢?
泓君:对,还有我觉得其实不管是电影还是播客,我觉得最打动人的东西就是人,他那种真情实感,这个东西是AI很难去取代的。
方励:是的,就像当年的无人餐厅,我来餐厅吃什么呀,我就是来看人的呀。我喜欢看人的不同表情,跟服务员可以交流。但进了无人餐厅,家里也无人厨房,人还有意义吗?活在人间体验什么呢?在科技里面是一样的,如果我们都过度的依赖工具制造出来的,当然你制造出来就跟你画画一样,一个画家如果说你的所有的照片、画也好,自己的原创的东西都变成了复制了,还有魅力吗?还有艺术可言吗?还有吸引力吗?都成了简单的复制和借用的设计了。
泓君:那您实际做电影的过程中,如果我们把AI当成一个工具来看,您觉得对您的电影哪些环节会很简单?
方励:那就非常对了。我刚做了这《里斯本丸沉没》,我要做数字模型。首先我要做海洋,海水有波浪,有波高有波周期,有流,这海洋的模型怎么建立呢?今天风是几级,能达到几级,海况好。这些模型在ocean graphic (海洋图形)的社群的里面早就是现成的。可这些CG公司、特效公司、计算机视觉公司,他不懂。你让他从头再去建模要费好大的劲。但是你把这些科技的,比如说海洋学的这些模型拿来,他又不能直接用,因为他的算法、他的数学模型这些做电影都看不懂了。
如果说以后我们把AI用上,我说那就简单。比如说,我最近在考虑的另外一个纪录电影,是关于空战。那我们见过的空战多了,不管是前人做过的电影,还是实际的纪录片,都有各式各样的俯冲俯仰、翻滚的各种姿态。如果你现在的AI和数据库里已经有这些东西,那就好简单,就避免重复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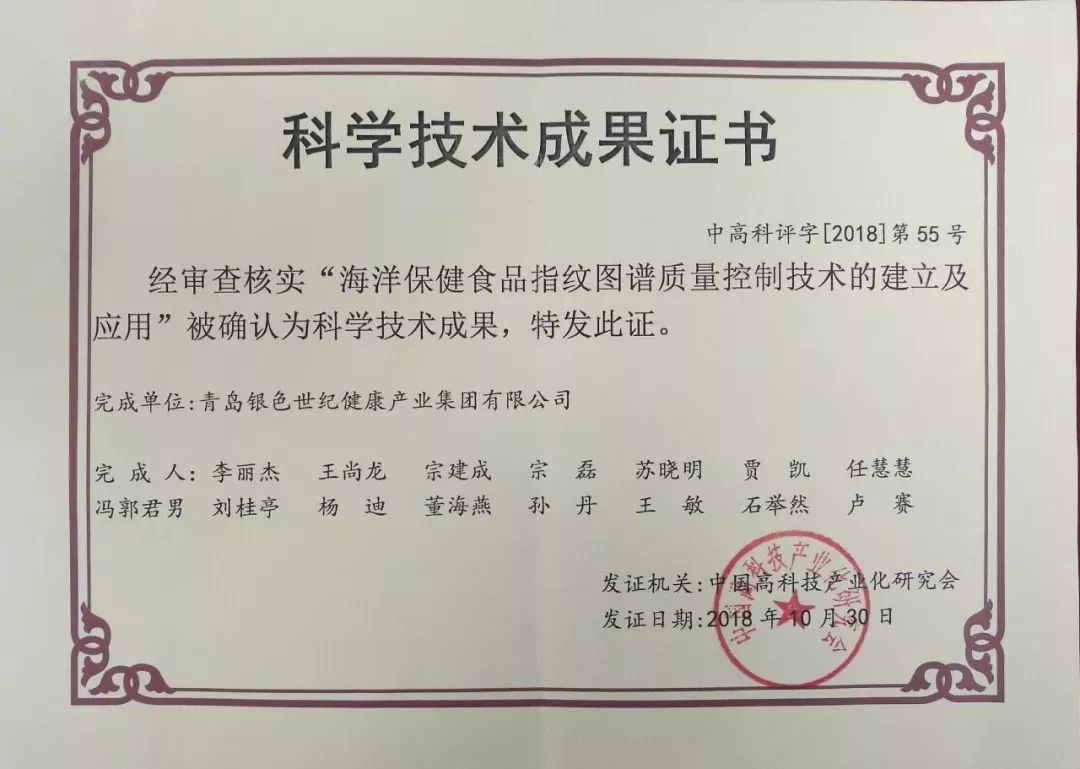
















有话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