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口的分化与等级制度的解体
- 体育资讯
- 2024-12-27 23:09:23
- 7
一代社会生活的形成乃至变异,必然意味着社会关系以及相关的社会秩序的变动。正是从这种角度而言,生活与经济、社会、思想、心态诸多层面有着密切的联系。
明朝人生活在一个社会转型时期,尤其是明代中期以后的社会,是以极具变化为其特征的。若将其置诸“社会流动”与“都市化”等范畴下进行考察,其时代的特殊性就更容易显现出来。换言之,晚明社会是一个转变过程,举凡人口的持续增长,经济的货币化和多样化(诸如农村的商业化,定期集市和小镇的激增,作物的专门化,手工业的发展,以及国内陆区性贸易市场的形成),社会流动的增长,租佃制与经济竞争的展开,以及政治秩序的集权化与系统化的互相联系,无不显示出它与前一时代本质上的不同。
自明代中期以后,农村人口开始分化。嘉靖四十四年(1565),当时有一位给事中凭借他在南北做官的具体观察,分析了其中的“病源”。他说:
大约豪宦连田阡陌,其势力足为奸欺,而齐民困于征求,顾视田地为陷阱,是以富者缩资而趋末,贫者货产而僦庸。
显然,传统“四民”中的农,由于“不乐其生”的原因,开始寻求两条新的出路:富者趋末经商,贫者货产僦庸。
(一)“游民”和“末作之民”大增
宋人王禹偁在上疏中曾说:“古有四民,今有六民。”其意是说,在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之外,宋代已经增添了兵、僧二民。明初刚立国,明太祖鉴于元末的社会状况,同样感到了从“四民”演变为“六民”的危害性。所以,明太祖立国的根本,就是将他统治下的臣民能重新安于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尽管他不得不承认释、道二民的存在,但他又通过对佛、道势力的严密控制,使其不能与朝廷争夺四民中的“农”这一民。换言之,他所执行的政策,其目的是为了让传统的四民各守本业,即使是医、卜,也强迫他们必须“土著”,不得远游。凡是“有不事生业而游惰者,及舍匿他境游民者,皆迁之远方”。
随着社会经济的逐渐恢复,朝廷的社会控制日渐松懈,社会流动日趋频繁,游民层的数量势必大增。《明实录》有一段记载,基本反映了这一事实:
方今法玩俗偷,民间一切习为闲逸。游惰之徒,半于郡邑。异术方技,僧衣道服,祝星步斗,习幻煽妖,关雒之间,往往而是。……今之末作,可谓繁伙矣。磨金利玉,多于未耜之夫;藻绩涂饰,多于负贩之役;绣文紃彩,多于机织之妇。
我们不无怀疑这段记载有夸大其词的成分,但确实道出了晚明时期的社会特征。但值得重视的是,所谓“游惰之民”的增加,一方面需要以“法玩”为前提,惟有传统的法禁形同虚设,尤其是“王纲解纽”的时代,才使得人们有了自由流动的空间;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只有经济的发展,国家财力的增长,才足以养活这些所谓的“游惰之民”。追求“闲逸”的生活,也不仅仅是反映了当时的“俗偷”,即一般所谓的风俗浇漓,或者说仅仅是士大夫阶层的专利,而是民间大众共同的生活追求。为了满足人们闲逸的生活,耒耜之夫、机织之妇的辛勤劳作无疑是前提,但生活的多样性确实也离不开那些从事磨金利玉、藻绩涂饰、绣文紃彩之人的工作。
“四民”层的存在,是以“皆专其业”、“各安其生”为前提的。按照传统的观念,四民各有定业,而后民志可定;而民志一定,则天下大治。然自明代中期以后,社会的变化已经不允许四民各安其生,四民皆专其业。朝廷赋役的加重,农村土地兼并的加剧,首先导致了传统社会统治基础的分崩离析,失去土地或者已经无法在农村安身的农民,不得不到城市寻找新的安身立命之处。于是,社会力量发生了新的分化,传统的四民之说已经无法规范社会大发展下社会各阶层力量的新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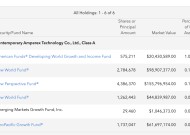













有话要说...